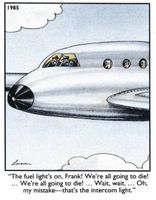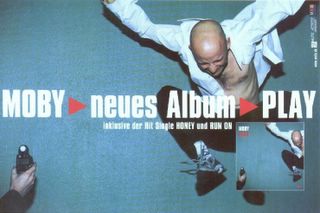《點燃生命之海》(The Sea Inside)是第七十七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,導演是亞歷山卓曼納巴(Alejandro Amenabar),他曾執導西班牙版的《香草天空》:《睜開你的雙眼》,及由妮可基嫚主演的《神鬼第六感》,男主角哈維巴登(Javier Bardem)則是威尼斯影展的影帝。
故事描述一個因意外而導致四肢麻痺的男人,在床上不能動彈,任二十八年的歲月流逝後,他一心尋求安樂死,對他而言,尊嚴的死亡比苟延殘喘的生存來得重要;生命是種權利,而不是義務,在他跟西班牙法庭訴求安樂死的過程裡,他體驗了許多挫敗,而中間,男人又與兩名女子纏繞出曖昧的情慾。
劇情,是依循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。

勒蒙桑培德洛(Ramon Sampedro)這名西班牙籍的男子,十九歲便搭上挪威的船,周遊列國,二十五歲時,他因跳水受傷,而至頸部以下全身癱瘓,之後他便不斷尋求合法自殺,1996年,在友人的協助下,他在病榻間寫完了一本叫做《來自地獄的信》的詩集。
詮釋勒蒙的男星哈維巴登是個妙人,他出身在一個演藝世家,最早想當一個畫家,後來他發現自己沒天賦,就轉行當作家、建築工人,甚至一度跑去當脫衣舞男。最後他在銀幕上找到自己的才華,兩度當上威尼斯影帝。
看完《點燃生命之海》,我覺得過多的讚美或解析,都是多餘的。如果它只是虛構,那麼大家都可以從各式各樣的角度,去發表些意見或道理。
可這是一個真實的、發生過的故事。
這樣的人生,不免讓我想起《潛水鐘與蝴蝶》這本書,裡頭的男主角鮑比,原本是法國時尚雜誌Elle的總編輯,才華洋溢、熱愛享樂,有一天他腦幹中風,四肢癱瘓,靠著眨眼的方式,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傳達給友人,而拼湊寫完這本書,出書後的兩天,鮑比就與世長辭了。
鮑比跟勒蒙不一樣的地方是,鮑比求生,而勒蒙求死。
勒蒙在抵抗外界鼓勵他活下去的聲音,跟同樣四肢癱瘓神父爭辯時,那如同卡謬的《異鄉人》,誰來仲裁這世間的一切的道德?是人還是神?是良知還是私欲?
勒蒙尋死的過程,任性地像個紈絝子弟,他對深愛且默默照顧守候他的家人咆哮,死神成了他最想獲得的玩具,金額就是一條命。
他拼足了勁,非得獲得這個玩具。
也許對四肢癱瘓、不良於行,腦中卻起伏豐沛洋溢情感,卻鎮日只能躺在床上,凝視窗外日升日落的勒蒙而言,上天開了他一個沈重的玩笑,他很想跟這樣的玩笑公平競爭,所以他幻想舉高雙臂,探望肉眼不及的無極虛空,當他真的可以尊嚴地決定生命的句點,這瞬間沒有誰贏了,對勒蒙來說,一切只是回歸,公平。
以上就是我的觀後感,其餘的,以我現有的生命跟勒蒙相較,我閉嘴。
這齣戲有些對白,讓我不禁想記述下來:
「當你必須完全依靠別人生活時,你就學會靠笑容來流淚。」
原本答應跟勒蒙一塊結束生命,癱坐輪椅上的女律師,最後卻因恐懼而拋棄勒蒙,而在病魔摧殘下,逐步遺忘一切,包括勒蒙。
勒蒙寫了首詩給她:
「出海去 出海去,在無重量的深度,夢境可以成真,兩個靈魂共償一個心願,你我的凝視,如回音默默重複:”更深、更深…”超越了血與肉,但我總是醒來,我總希望能死去,嘴唇永遠牽纏在你的頭髮中。 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