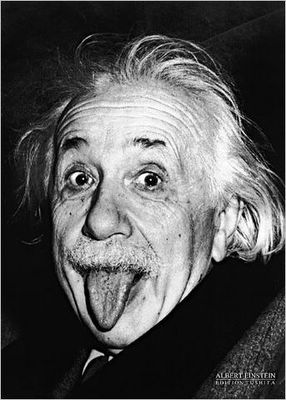
我是個老梗,年過三十,不好不壞、有好有壞地在社會的大舞台上,佔據一個位子,出奇乖巧、其實死扒不放地蹲坐於此。
我翻索著腦袋中的常識詞彙,中學時代,老師曾教導過我關於「中流砥柱」、「中堅份子」的用語,二十出頭甫進入公司行號的階段,我學會「老不死」這字眼;成長兼成熟的路上,跌跌撞撞的經驗教導我學會很多道理,現在他們叫我「老屁股」,總之關於「中」、「老」、「熟」呀的字眼,如今都冠在我的頭頂上。
這是我名片上,真正的職稱抬頭。
是的,我正處在前中年期,毫無異議,早就知道這一天、這一切勢必通通到來。若干年前的某個清晨,我向上帝買了張入場卷,祂當時就跟我講清楚遊戲規則,降臨於世的這一秒,我將打開一個超大型遊樂場的門,進去裡面翻滾走跳。起初我沒能力站立,後來慢慢爬行演化成人,先擁有光滑的肌膚,再逐漸冒出痘子;陷入擠青春痘的焦慮期沒多久,魚尾紋突然間揚起。
歲月的發生,總在令人措手不及的時刻。
「不過,煩惱總有新鮮的。」上帝祂對我笑說。
進去這個大型遊樂場時我便明白,每個人總有一天是要出場的,大家都是從很小一隻地爬進會場,搖擺著已退化的無形尾巴,逐漸變成很皺的一隻,被抬出會場。
最近的我,恰好玩到遊樂場中間部位的海盜船,一切都不怎稀奇,前頭我已經玩過好多種遊戲,高空彈跳、雲霄飛車等,只不過,現在坐的這艘海盜船並不平靜,船身邊冒出一堆素未謀面的小海盜,臉上畫滿做作的假紋身,叫囂聲比鬼屋裡的假鬼還要拉高分貝。
他們看起來像是一個團隊,有個名號叫做「七年級生」。
真好奇這些小鬼是打哪來的?

他們一下子就湊過來跟我平起平坐,語氣非常熱絡,讓我懷疑曾在遊樂場的哪個角落裡,跟他們坐在同一個咖啡座,只是經歷過的遊戲機太多,不小心忘了他們是誰。
「你們前面玩過了嗎?」我問。
「沒!我們一下子就在海盜船這裡了!」嗓門大得很。
「所以你不知道前面有……」我說。
「當然不知道!什麼玩意啊?那是老掉牙的梗!」驕傲不已。
「但是,你竟然會不懂……?」我質問。
「什麼?你欺負我?嗚嗚……不跟你這老梗玩了,我要回家!」他們跺著腳,含淚吵著要閃人。
我很想跟他們講一句:「進到遊樂場後,就沒有閃人回家這碼子事情,不管你是從哪號遊樂機玩起,你都得伴隨著歲月老去,去體會每一款機型。有些讓你玩得很High,有些讓你玩得很慘,無論如何,進場後就沒得棄權,每個人終究會玩到滿身疲累地爬出場,這時間點,不會是由你決定。」
回想我所經歷的遊戲年代,不像現在如此資訊發達;我們是剛從壓抑中初被解放的小鬼頭,上有教科書下有淵博的無底洞;青少年時期的我們,聽著Erou Beat踩跳著凌亂的霹靂舞步,那時候MTV台剛開始在台灣開播不久,傻傻地看著瑪丹娜唱著〈宛如處女〉假高潮,乍開放的社會環境,讓我們興奮又開懷地腎上線素遽升。
跨國的唱片公司剛進駐台灣,我們這群嗑音樂的小鬼剛開始轉大人,懷抱熱血幻想在其中揚名立萬;那年代,國際中文版也才剛在台灣冒出個端,攝影師拍著Slide研究哪些畫面該正沖負?美編還在手工完稿,剪貼圖形如同在拼湊未來夢想的角度。
我們的上頭還有老老梗,不管那些大人是在說箴言還是廢話,我們都不敢多嘴,只能觀察、發問跟學習;大人聊到Bob Dylan,我們不會馬上反應回嘴:「那是個什麼巴拉圭?」
我們沒有像ASOS這種當年還是個小女生,就敢飆著連珠砲的嘴賤,無聊當有趣、嘻皮笑臉扯爛稀泥的偶像;我們只能在背地裡悠悠抱怨,沒有人會瞪眼、撐鼻地出來靠北。
小鬼們速食化的生活,讓他們甚至變得相當無情,反倒是我身邊的老梗友人,對這世界仍懷抱著些虛無的浪漫情操。
真真切切地愛過、痛過、活了一回。
當初,我們也想跟隨大人的腳步,但絕對不是坐到他們身邊滿嘴亂屁;我們每個人的家裡,或多或少都有些時潮演變的歷史書,講到更古早時的搖滾女歌手,我們絕對不會說六○年代的Janis Joplin只是個什麼yo yo yo 的shit yo。

我們能做的,就是學習跟累積前人的知識,再試圖連結到自己的時代;我們不敢說自己有多虛心受教,但至少,我們會擔憂與害怕自身的不足,肯下功夫去耕耘。那天我跟一個朋友在MSN上聊到:「現在的小鬼表面上搞得很炫,但實際上,他們很淺。」
「有淺嗎?」朋友說:「沒有深度,哪來的深淺可說。」
他的這番話,真是一針見血。小鬼們的喧嘩聒噪,已經令我這個老人相當不耐煩,我忍不住跟另一枚朋友訴苦:「乾脆點,準備去養老算了!」我懶得聽這些小孩的頂嘴與廢話,更不需要把自己走過的路、經驗,傳承給這些目空一切的傢伙。
不過,換個角度想,這群小鬼們的天真「爛」漫,對我們這群六年級前段班以上的中年人也是有優勢的,他們的無知與自大,倒是化解我們不少中年危機,以致於我們不用太擔心會被這群既不知古,就愛亂哈拉今的三腳貓動輒取代。
無論如何,我仍待在這艘海盜船、這座大型的遊樂場內。
除了對這票《蒼蠅王》 生厭外,還有一點可提,就是我們這群經歷過封閉與開放交替的老梗,骨子裡的傲氣與火爆性格,並沒因時間的流逝而消減,也許我們隱藏得比較好,也許表面上,耍嘴皮子講賤話的功力,我們不敵小鬼們流轉。
可一旦真要點燃了我們的梗,怒火燒起來,是不會比小鬼們的青春烈焰溫度低的。






